E·H.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1892—1982),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学家。毕业于剑桥大学圣三学院,并在剑桥圣三学院任高级研究员。1956年当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在史学理论方面的代表作《历史是什么?》堪称经典。《历史是什么?》本是卡尔1961年1—3月在剑桥大学“乔治·麦考利·特里维廉讲座”(The 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 Lecture)所作的系列讲演,1963年由纽约艾尔弗雷德·A.诺夫(New York·Alfred A. Knopf)出版社正式出版,并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世界各国。我所阅读的是由陈垣翻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历史是什么?》2007年版。
历史是什么?这是历史学中的最基本命题,也是历史研究中众说纷纭、需要长期讨论下去的问题。一般认为,历史至少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已经过去的事实,一是对过去事实的记载与研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一书中指出:“历史由一大堆已经确定的事实构成。历史学家可以在文献、铭刻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那里获得事实,就像在鱼贩子的案板上获得鱼一样。历史学家收集事实,熟知这些事实,然后按照历史学家本人所喜欢的方式进行加工,撰写历史。”[1]卡尔用很大篇幅分析了历史与历史学家的关系。众所周知,历史的撰写和研究,通常也只能依据当时遗留下来的文献,而这些遗留下来的文献,就包含着文献编写者的主观思想,就如卡尔所言,历史学家是以“本人所喜欢的方式进行加工”。中国古代政治史为例,“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思想一直存在,对胜利者极尽美化、对失败者肆意诋毁比比皆是,这似乎成为了中国历史千古不易的规律。尽管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但任何人记载下来的历史都不能避免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情的影响,因此也许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大家能接受的客观、真实的历史。
在阅读卡尔的这番论述时,我想起了曾经阅读过的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也对此有过阐发。汤因比提出要从整体观念去审视历史,认为“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某个特定的国家、文明和宗教,因恰好属于我们自身,便把它当作中心并以为它比其他文明要优越” [2]。对于这样的历史学家来说,前人的研究视角和立场,反而成了全面认识这个世界真实景象的障碍。
因此,我觉得历史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是探讨问题的框架,并给时间中的事件赋予其独有的意义。相对的,历史学也从来不是尽其所能的积累大量的事实,进行简单相加,而是历史学家在特定时空背景下提出问题,然后援引证据来支持自己的回答。其中的证据就是各种史料。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尽管要复原历史的真是确实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有一个前提不会变:历史本身是真实的,是客观存在过的事实。正如卡尔所言:“相信历史事实的硬核客观独立于历史学家解释之外的信念是一种可笑的谬论,但这也是一种难以根除的谬论。”[3]所以,我们必须承认,绝对的真实历史是永远无法获得的,就像绝对真理一样。而且历史科学有其自身的局限,它的研究对象只能是过去,而不是现在或将来。历史既是全人类的活动,又是一个个具体人的活动,而人的生命与历史想比是极其短暂的。一个人,无论多么伟大,只要没有留下记载,他的行为和思想就会随着时间不断消减。即使一个活着的人,对他过去的研究也得依靠当时留下的记载,直接、间接的,自己的、他人的,而不是由他本人现在来重现。
卡尔关于历史事实与历史学家的阐述,给我们如何正确使用历史研究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诸多借鉴之处。例如他在书中写道:“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不以也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得头脑折射出来的。依据这一说法, 当我们研究一本历史著作时,我们首先要关心的不是这本书所包含的事实,而是这本历史著作的作者。”[4]在读一些历史著作甚至是史料时,我们往往关注于内容本身而忽略了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作者人生与学术经历。这样往往容易让我们对历史著作缺乏理性的认识。而对作者的研究,一定要充分考虑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与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个体,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社会的产物;研究历史的人必须学会从这一双重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
关于历史的功能,卡尔的论述也相当精彩。他说:“我们只有根据现在,才能理解过去;我们也只有借助于过去,才能理解现在。使人能够理解过去的社会,使人能够增加把握当今社会的力量,便是历史的双重功能。”[5]在我看来,历史研究的基本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要在复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探索以往的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 就像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为了探索该学科的内在规律一样。因为历史受众多偶然性的影响, 历史发展会显出曲折性、多样性和出现各种具有个性的历史人物与各具特色的历史事件。这是真实的历史。可是, 所有偶然性对历史的作用, 都不可能超过一定时期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总体状态的制约作用。恩格斯形象地把生产方式称之为历史波动的中轴线。全部偶然因素的作用都是以它为中心上下摆动。大量偶然性的存在使必然性的实现更为丰满和多样, 因此历史的色彩从来是丰富的斑斓多样的。但这不会改变社会生产方式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原则。历史周期越长, 生产方式最终的决定作用越明显。这种对于历史内在规律的探究,才是人类不断研究历史的源泉与动力,也是历史最具魅力的地方之一。
[1] [3][4][5] [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陈垣译,第90、93、106、146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
[2]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第1页,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参考文献:荻冬眠熊:《我心目中的历史学》,北京师范大学,200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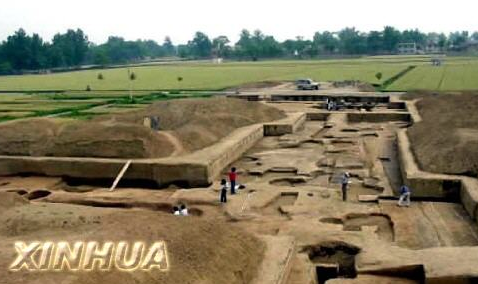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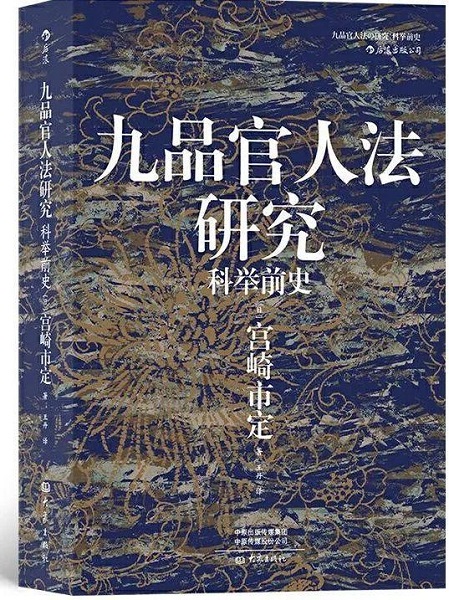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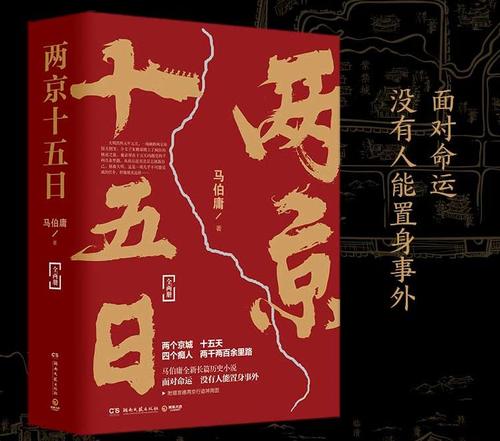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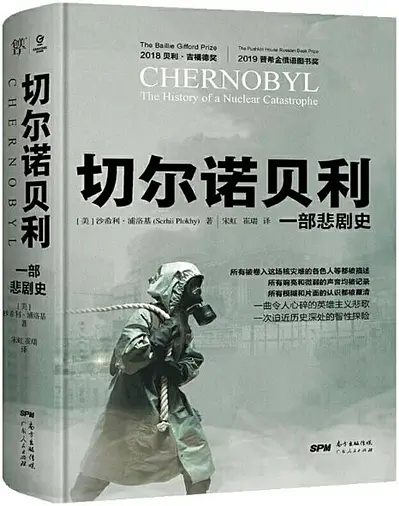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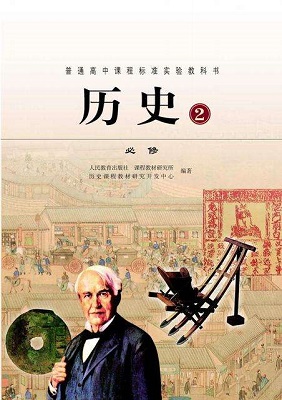

我又回复了
有荻冬眠熊!~~
@喵小维这都被你发现了
历史学家是以“本人所喜欢的方式进行加工”。中国古代政治史为例,“胜者为王败者寇”的思想一直存在
写的不错 求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