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作为我国18世纪中叶一部伟大的长篇章回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如鲁迅所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作都被打破了。”因红楼梦的研究而产生的一门“红学”,在世界上已经公认为是足以和甲骨学、敦煌学鼎立的“显学”。红楼梦的研究在早期文学评论的基础上引入了考据学的观念与方法,使得红学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在红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引派、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小说批评派,红学界的百家争鸣促进了红楼梦研究的深入与发展。
红学有很多分支。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者周汝昌先生曾经指出红学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四大分支学问即曹学、版本学、探佚学、脂学。研究曹雪芹的身世,是为了表出真正的作者、时代、背景;研究版本,是为了恢复作品的文字,或者“文本”;探佚即研究八十回后的情节,是为了显示原著整体精神面貌的基本轮廓和脉络;研究脂砚斋,对上述三方面都有极大的必要性。
《红楼梦》版本的复杂繁多,堪称历史之最。按其流传方式,主要分为过录传抄本和刻印本。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由程伟元主持、高鹗参与修订整理并首次以木活字排印问世的《红楼梦》,胡适称其为“程甲本”,这作为早期抄本和后期刻印本的分界线。在这之后,《红楼梦》不断翻印,使其在社会中影响随之扩大,虽然诸多印本中都有版本上的异同,但所据的底本基本上是程甲本。程甲本是百二十回本,删去了所有的脂砚斋批语,并且其后四十回基本上认为是高鹗续写的,续书中的内容经考证与曹雪芹原本的小说整体构思相差甚远。在程甲本问世之前,《红楼梦》主要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民间流传,并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脂砚斋的批语与《红楼梦》原文在书中是同时出现的,脂砚斋的批语对于理解曹雪芹的创作思路和小说后四十回的情节都具有重大意义。早期的书名多数为《脂砚斋重评石头记》。但是当今已发现的手抄本却仅有十一种,而且多残缺不全,存留最多的也只是八十回书,今各手抄本为百二十回者多为藏书家后来配补的。早期的这些抄本,几乎都是过录本,其状况也极为复杂,有些甚至并非过录于1791年,过录所据的底本有些也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本子拼合而成。尽管如此,这些过录本所据的最初祖本,都形成于1791年之前是无可置疑的。手抄本因为较之程甲本更多的体现了曹雪芹著书的原貌,有助于我们认识曹雪芹创作的那个“真本”《红楼梦》,所以特别具有研究价值。可惜的是现存的没有一本是曹雪芹的原稿和定本,均为过录甚至有转抄三四次之后的版本。
目前最后价值的三个抄本为甲戌本、己卯本和庚辰本。这三个抄本所据的最初底本产生的年代均为曹雪芹逝世之前。甲戌本仅存十六回(1-8,13-16,25-28),书中第一回在介绍《红楼梦》的书名变更时,有一句其它版本都没有的“至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语,故命名为甲戌本。甲戌年,即乾隆十九年(1754),要注意的是这并非是甲戌本的版本形成年份,更不是现存这个本子所抄写的年代,而只是现存本子抄录所据的最初祖本的形成年份。甲戌年是成书过程中涉及到的最早年份,其他版本所提到的年份都晚于甲戌年。所以甲戌本在所有版本中具有重要意义,书中有很多不同于其他版本而独有的内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红楼梦》最初成稿时的面貌,从书中的整体结构、内容和脂砚斋批语可以推测,甲戌年《红楼梦》的初稿虽然尚有留阙待补的局部,但整体已经完成,并开始修改。
更为重要的两个版本是己卯本和庚辰本。现存己卯本仍是过录本,而且还经辗转传抄,因书内确有“己卯冬月定本”而命名,该版本现存四十三回(1-20,31-40,55-59,61-63,65-66,68-70)。书中因为存在避两代怡王名讳,即允祥和弘晓,而被认为和怡亲王府有关,而历史考证怡亲王府与曹雪芹家族联系密切,故该书的意义更为重大。庚辰本也是因书内有“庚辰秋月定本”字样而命名,现存七十八回(1-63,65-66,68-80),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庚辰本和己卯本有很多共同之初,两者的联系相当紧密,比如同时存在避讳,抄录的笔迹也有相同之初,大量的批语都是相同的,前十一回基本上没有批语等等。现一般认为,从乾隆己卯(1759)之冬到次年庚辰(1760)秋,曹雪芹跨年度完成了《红楼梦》定稿本。至今还没有发现在1760年后至曹雪芹谢世的这几年间其他形成的版本,故这是曹雪芹生前的最后定本,其意义相当重大。
值得一谈的是北京师范大学也曾经发现过一本手抄本的《红楼梦》,被学界命名为“北师大本”。北师大图书馆于1957年由琉璃厂书店购入一部八十回抄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直至2000年被北师大博士生曹立波无意中借出,发现文本字体工整并有大量批语,书中还有“四阅评过”的标记。此书一经发现,立即引起了红学界的关注。红学家周汝昌、冯其庸、蔡义江等先后对此书进行过鉴定和研究,并撰文就该版本的特点和与其他版本的关系进行过讨论。冯其庸认定北师大本是据北大的庚辰本抄的,并根据笔迹推断该本的抄录者即是前面提到的己卯本的原收藏者陶洙,但也有人认为北师大本虽然具备了庚辰本的特征,但也与现存的其他版本也有关系,无论在正文还是批语上都有自己的特色。周汝昌认为北师大本不仅有异于北大本而同于其他版本,而且有独异众本的异文,根据文字的对比,认为北师大本是具有独立价值的旧抄本,与北大本没有直接关系,它的抄写年代可能要早于今北大的过录本。北师大本的发现和研究,进一步激发了红学界对于版本学的研究热情。
现存的《红楼梦》手抄本数量相对来说甚少,其实早期手抄本的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如程伟元曾写道:“是书沿传既久,坊间缮本及诸家所藏秘稿,繁简歧出,前后见错。”乾嘉时文人墨客多以谈《红楼梦》为韵事雅事,如经学家郝懿《晒书堂笔录》:“余以乾隆嘉庆间入都,见人家案头必有一本《红楼梦》。”人们也时常提及竹枝《草珠一串》中的一首诗中的“闲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因此民间的抄本数量相当可观,虽然至道光年间《红楼梦》一度被列为禁书,但是从当时的流行状况来看能够存世至今的抄本当不止目前的十一种,还有更多的或许更珍贵、更有研究价值的版本落于民间。20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了一个异于其他手抄本的所谓“靖本”,但一直未曾露面,发现者称其已经迷失,但其抄录下来的一些独有的批语也引起了红学界的广泛讨论。当今《红楼梦》的版本学急需新版本的发现,民间所藏的抄本逐渐被发现的话,那么对于《红楼梦》的认识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对于红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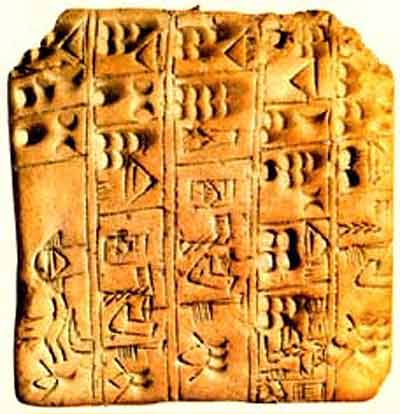

原来还是个红学专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