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前我曾一度以为独轮车是最傻缺的发明。
你又不缺那点轮子!又费不了多少木料!你搞两个轮子就怎么了?一个轮子多孤独!像平板车一样顺顺当当走就可以了嘛,非搞成一个轮子,摇摇晃晃的。不但要往前推它,还要分出很大一部分精力和力气来掌控平衡。而且都不能拉着走!
小时候奶奶家倒垃圾是用一辆独轮车,又一次我自告奋勇要去推着车倒,结果刚一起步就把车给弄翻了,垃圾撒得满院子都是,人也差点摔倒。叔叔伯伯们在屋檐下乐得嘎嘎大笑,真是个窝囊废!
对于这种车,如果你没有强健的肱二头肌和肱三头肌,我劝你还是放弃吧,因为一颠簸,车就晃,你hold不住,就倒了。
后来有人说,独轮车的优势在于不论什么样的路,田埂、木桥、窄巷都能走,胜在便捷。
这一点,如果不了解几千年来中国道路的情况,是不会理解的。
二
当年秦始皇一扫六合,后人称之为有三功: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
为什么车同轨会被提到这么高的高度?你看现在满大街跑的小汽车大汽车,轮距都不一样,不都一样撒丫子狂奔?
陈胜吴广当年走到大泽乡的时候,会天大雨,道不能行。为什么路下点雨就不能走了?
好了我也不打算卖关子过渡了。这其实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当年的路,是什么路?
土路。
下了雨,就是泥路。软乎乎的,一走陷很深,确实不能走。
确实就是泥土地,光光的什么都没有。屡次下雨,屡次天晴,来往的车辆就碾下了深深的辙印。在乡野土路上,这种车辙往往能达到一尺多深,车辙的中间是牛马等牲口走的路,也是深深的一道沟,叫牛蹄心。那时候的路就这样,一条路、两条辙。如果是在窄路上,“车不方轨”,碰上对面来车,就要会让,这实在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你要鞭打你的牛,费力把车从深深的车辙中拉出来,让对方的车过去,然后在回归原辙,继续前进。所以,外公讲,那时在小路上往往能看见两个车把式大眼瞪小眼,争论着谁应该让谁。
所以,改弦易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改弦,要承担弓断的危险,易辙,要使出牛力气。老祖宗说话,可真形象!
来来回回的行走把车辙里的土壤压的如此坚实,前不久在陕西境内发掘秦直道的遗址,就是靠几条不同宽度的车辙,和几条牲口踩踏出来的“牛蹄心”来确定方位的。啧啧,这种力量是如此的巨大,甚至两千多年的风霜雨露都没能抹去土地上的印记。

(此图截取于人人网网友黄鹏的相册《一百年前的祖国》,类似土路上的车辙相片一直寻而未得,忽然得见,如获至宝,2013年9月1日补充入日志。一幅图片搞得我半篇文章似乎在说废话,向黄鹏同学致敬!)
所以,能顺顺畅畅沿着前人压好的车辙前进,是一件很愉快的事。
如果你是一个造车的人,你面对全中国亿万条土路上的亿万条车辙,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自己造出来的车要能合辙,能顺畅地沿辙而行。
车轮碾下的印记叫辙,车轮之间的距离叫轨。轨的长度就决定了辙的间距,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六国之间道路上的车辙彼此混乱不通,很影响交通。而车同轨之后,从此天下互通,修建三十六驰道,一直道,从此在交通上奠定了中国大一统的基础。
别小看交通,当年阎锡山和蒋委员长闹别扭,在修铁路的时候就耍了心眼。本来委员长要修大潼路,就是大同到潼关,修成标准轨距,和全国互通。结果阎锡山非要自己修,修同蒲线,从大同到蒲州,蒲州离潼关很近的,可以看成是同一条路。却修成了米轨。从此外省的车不能进山西,山西的车要出省的时候,把车轮往外一调,却能顺顺畅畅出来。凭着这些花招,闫老西儿做了山西38年的土皇帝。
所以,当年路上行走的马车牛车,只能和如今的铁路做类比,不能和公路作类比。当年上历史的时候,前期没有介绍古中国的路况,光秃秃地说了一句车同轨是秦始皇的功劳,大家都不知所云。
甚至有人说车同轨是统一了全国的道路宽度,这简直胡闹。“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周礼,考工记》里就明确规定了,轨是两个车轮之间的距离,古代就根据主干道、次干道和郊区道路制定了不同的宽度标准,南北向的大道要宽达九车道,绕城高速就是七车道,郊区公路就是五车道。至于极窄的道路,只好“车不能方轨”,也就是说不能并驾齐驱,只有一车道。就比如“太行八陉”中的井陉口,那就险要而窄,至今还在山石上留存着自秦以来压下的深深辙印。车把式们就该在这儿大眼瞪小眼了,操娘骂祖宗地争论谁该“易辙”了。
你说秦始皇又不傻,把他阿旁宫门口的大道和太行山中的小径统一成一个宽度,脑抽了?甚至更有以郭沫若为首的人群将“车同轨”引申为统一风俗习惯,那就更是想象力丰富了。
结论只有一个:车同轨,就是利用政治暴力规定统一了车轮之间的距离,因此从辽东到西蜀,从秦淮到河套,都能一路畅行无阻。交通天下,便利九州。
虽然规定得很简单,但意义不下于书同文。
对了,现在车道都是双数,为何周礼中都规定是单数?
很简单,中间的一条是给天子出行留着的。
三
古人讲“闭门造车”,来形容不问天下形势的人。为啥不说闭门造飞机?因为飞机的制式不同,只要公输班造得好,一样能上天。而车不同轨,不管是谁造的,都是废木头一堆。所以,这个成语完整模式是这样的:闭门造车,出门合辙。
再讲讲合辙押韵的事儿。
车轮“嚯嘞”一声合辙而入,那种舒畅感是无以复加的。而戗辙而行,那种费力、难受、滞涩感又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写诗歌的时候要讲究音韵的时候,就用“合辙押韵”来形容。再说一遍,古人说话,是极其形象的。
老家将一件事儿有先例可循,叫做“有辙套”。
如果路上无辙,或者车不合辙,又让你跑运输的话,纵然是久历江湖的车把式也要叹一句:“卧槽!没辙啊!”
以前看过一则故事,是讲历史的惯性的。说美国宇航局运载火箭的直径直接受到古罗马帝国马屁股的宽度的影响。因为人们根据马屁股的宽度制定了车轮的轨距,车轮轨距决定了车辙的间距。这个间距影响到了英国人造铁路时制定轨距的标准,轨距标准决定了美国山脉中开凿隧道的宽度,隧道的宽度就限制了通过铁路运输的火箭的直径。
这就是历史的惯性。
所以,开头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独轮车的产生是尤其历史原因和物质基础的。不论是什么样的辙,什么样的路,独轮车都可以走,因为它一个轮子嘛!
四
这种路况,一直持续到民国后期。
倒不是因为中国的路都硬化了——因为还没那么多钱,路还是土路。而是因为横行中国几千年的“包铁尖脚车”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而是皮车。所以纵横中国大地上的亿万条车辙从此消失了。
皮车不是用牛皮马皮做的车,而是胶皮车的简称。胶皮也就是橡胶,这里说的皮车也就是用橡胶做轮胎的车。
橡胶做轮胎很好,减震、耐磨,而且受力面积大,压强小,不至于在土路上压下深深的车辙。
所以,路稍微泥泞一点也能走,走几遍也不至于压出半米深的车辙来。所以,任何轨距的车都可以在路上走了,从此路上就出现了大大小小各种形式的车,不再像是以前的一贯制。走的时候也不必按着一条车辙走,因此方便了。
在橡胶出现以前,怎么解决车轮材料问题呢?
首先是耐磨问题,其次就是在泥泞道路上行走的问题。
解决第一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在木轮外面包一层铁,用熟铁锻造好一节一节的带钉的铁条,用钉子钉在木轮外缘。
解决第二个问题有两种思路,一是尽量让车轮不至于陷得太深,这样就比较容易行走。这就要减小压强,履带的出现就这么出现的,橡胶轮胎也走的是这一路线。
二就是索性不考虑下陷量,我只要保证陷进去能够快速利索地再拔出来就好了。那按照这一思路,压强就是第二位的,第一要保证的是车轮与泥土的粘滞力要小。车轮与泥土的接触面就要小,越小粘滞力越少。所以古人就把车轮的宽度做得很窄,很尖。
当然,这样虽然车轮不会陷死,但还是会下陷的,所以底盘必须要高,以留出下陷的冗余。所以车轮就要高大,这不仅仅是出于礼制和威风的考虑,也有非常实际的用处。
这样的道理,只要脑子明白,想一想就清楚了。不过这年头儿除了事例论证外,还要掉一掉书袋,才会显得高端大气。那么,咱就给你找出一条经典来。
楚狂接舆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赉金百镒,造门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镒,愿请先生治河南。”接舆笑而不应,使者遂不得辞而去。妻从市而来曰:“先生少而为义,岂将老而遗之哉!门外车轶,何其深也!”
咱就不讨论接舆是如何的清高,单说那位“不调查就随便乱发言”的老婆批评接舆的话:“你这一辈子的清高咋就晚节不保了呢?看看门外的车辙,竟然那么深!”车轶,就是车辙。这说明了两个情况,一是古代道路车辙深深的情况是存在的,甚至是走一遍就会在泥土路面上留下深深的辙印。二是"尖脚车"的下陷量还是很大的,必须做得车轮大底盘高。
所以,古代的车都是高大的车轮,尖尖的轮缘,包着铁皮。在我们老家,管这种车就叫“包铁尖脚车”。

五
造车轮也很有意思。以前读荀子的《劝学》一文,中讲到“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说的是把一跟木条经过烤、掰的工序,最终由直掰弯,弯成了一个圆圈。以前我也一直以为做车轮一贯是这个工序,其实不然。
外公聊到春泉涌的隔壁有个木匠铺,专门做车。车轮的外缘那部分,也就是辋,是用一块块木块拼接而成的,不是一整条木头弯成的。这也好理解,毕竟掰弯的东西机械强度差,使不得。
造车轮的首要一道工序是“凿毂”。毂(gu)就是车轮最中心的那个东西,老家叫毂葫芦。老子里说“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yǒu)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大谈无的奥妙。
咱今天先不聊哲学。
这里讲的毂,作用是把辐条都攒凑到一块。但是,它的作用也仅仅也就如此了,并不承担辐条传下来的应力。
那辐条的应力谁承担呢?它们彼此互相承担。
是这样的:辐条也不是老子时代的三十根,而是十八根。毂是个木制大圆块,在这个圆家伙中间凿一个空眼,是将来插车轴的地方。周身凿十八个眼儿,是将来插辐条的地方。这插辐条的十八个小眼儿和那个插车轴的大眼是互通的。
这里有看官就不理解了,这十九个眼儿一通,那车辐条不久直接插到了车轴上了吗?应力直接压在轴上,那摩擦力该有多大,还怎么走?
答案是,辐条的末端都是楔形的,这十八根车辐条彼此紧紧地攒凑在一起,挤压的很紧,就天然形成了一个圆孔,这就是老子讲的“当其无”的地方。因此,毂仅仅起到一个控制与安排的作用。如果毂就硬生生去抗车辐传过来的压力,质地再好的木料也要被压坏,只能让辐条们凑成一个轴承,用挤压抵抗应力。所以老子讲十三辐共一毂,而不是压一毂。古人大才!
震撼不?当年我听外公讲到这一段的时候,就震撼的无以复加。
但是这种题凑或者是辐辏的做法,是中国一贯就有的,做拱券时候砖的叠涩,做墓葬时“黄肠题凑”的手法。聚微小以成大势,叠分散以成整体。再加上聚而不集,留有空隙,留无,才有了“车”之用。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然,这个辐辏而成的圆孔只是承力,和容纳车轴。真正和车轴摩擦的还是毂葫芦上大圆孔镶嵌的铁皮。
十八根辐条插入毂中,敲打平衡,再将辋木安插在辐条端,用铁钉钉好。再将包铁钉在轮缘,毂口也用铁皮包好,一个车轮就大致做好了。现在来看,十八根木条集聚在一起,很有气势,所以古人就把那些汇聚八方之地、交通要道叫“辐辏之地”,包括后来讲的辐射,不也就像这辐条一样由一个点发散到四面八方?再重复一遍,古人讲话,真特么的形象!!
车轮几乎是古式车辆上的灵魂部件,最具技术含量,最美观,也最有气势。那辐辏之气势,林列之精巧,甚至古人定制车辆等级的时候,车轮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考量标准。
车轮做好了,相当于造车过程中最具技术含量的工序完成了。凿毂的手艺、辐条的打制,最后辐条的安装、调整都很有学问,直接影响到后续车辆的行走、摩擦系数、使用寿命。剩下的活儿,基本木匠就能干完,做车架,做车辕,车轴,然后组装到一起,轮子按上车轴,用一个叫“辖”的东西插上。
再接下来就是铜活、漆活、皮活,做一些配件、装潢、保护的措施,就是后话了。
据说,毂是核心部件。眼儿要是凿得不均匀,辐条安起来就疏疏密密,完全没法子用。一个学徒进入车铺,每天的工作就是凿毂,车铺的角落里堆放着大量凿好的毂葫芦,都是标准化生产,以备于做车轮的时候用。

民国时候大轱辘木头车的实物图。货车,我没骗你们啊!(本文转自人人网,作者乔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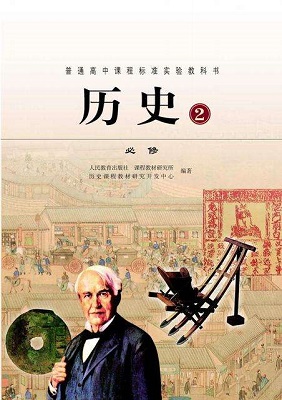






网站做的好棒哦
过来看看
说得不错,有收获,顶一下
图片都显示不了了吗?
@Go读物是的 所有用中文明明的图片都不显示了 太杯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