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11年,武汉三镇上空一面十八星旗高高飘扬,宣告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闭关锁国、王权体系牢固的传统社会,在一番头破血流后,终于选择了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鲁迅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涂饰太厚,废话太多,不容易察出个底细来。为了透过纷繁的云雾看清这段震惊世界的历史,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开玺教授,听他从一个专业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细数这一段历史的波澜。
(一)革命,只盼天下为公
世人常说“武昌起义”和“共和肇始”,事实上,“辛亥革命”这个概念在百年的演变过程中被不断赋予新的定义和内涵。早在1912年,署名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和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就提出这一名称。“很多人讲辛亥革命是国民党人宣传的结果,但我们现在讲的‘辛亥革命’与1912年时的‘辛亥革命’在内容和概念上都有一定的区别。我们现在讲的辛亥革命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下限到1912年清帝退位,或者到二次革命失败或许还可以更远。所以,现代意义上理解的辛亥革命在时间跨度上是一个过程,而当时这个概念所指的是辛亥年发生的推翻清王朝的武装起义;现在讲的辛亥革命的时段比较长,指的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样一个内涵,这就与当时所指的一个简单的武装起义有区别。”
实际上,革命的概念有严格的内涵限制。王老师认为:革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来说,某领域中的重大变革都可以称为革命,比如思想革命、文化革命、史学革命等;但严格意义上的革命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指的是被压迫阶级以暴力手段推翻旧的统治、旧的社会制度、旧的生产关系,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生产关系。“革命的重要内容必须要有旧的社会制度,不是推翻旧的社会制度,不叫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周易》有云:“顺乎天而应乎人”,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暴力反抗,为什么秦王朝、隋王朝被推翻了,我们现在不把大泽乡起义和瓦岗军起义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革命?就是因为革命有一种进步的规定性,能符合社会的发展方向。“革命必须要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符合人情、符合人理才能叫革命,违背人的利益不能叫革命。”
(二) 历史,只愿风雨无阻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革命”时期,当革命走下历史的神坛,辛亥革命不可避免地被贴上“激进主义”的标签。一些人甚至开始怀疑这场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认为即使没有这一枪,中国也可以在清末新政、立宪运动等变革的开展下,温和地、渐进地走上现代国家之路,而辛亥革命却打断了这一切。王开玺教授对这种观点很不以为然,他强调“一个社会是采取和平改良还是暴力激进的方式,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要看他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具备这种条件”。
鸦片战争后,中国改良浪潮不断。清政府内部有以魏源、林则徐为代表的改革派,之后的洋务运动也想要通过学习西方长技来改变中国。但是这些改革成效如何?它们并没有解决当时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历史发展的连贯性又决定了它不会为谁驻足停留。“从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到1912年清政府灭亡,72年时间。历史哪里有时间让它慢慢地去改?”很显然,清政府并没有赶上历史的步伐,最终被甩下了。
然而,即使历史给了足够的时间,皇帝又是否真的愿意放弃“一呼百应”的特权?在1911年5月8日(宣统三年四月十日)出现的“皇族内阁”证明,存在了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经成为每个皇帝改不掉的“习惯”。还有更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统治者有没有能力力挽狂澜。当时的中国已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国家,统治者自身的思想观念也已过时,面对 “立宪”字眼,恐怕也是力不从心。
实际上,没有人生来主张暴力。从具有改良性质的《上李鸿章书》(1894年)可以看出,孙中山曾对清政府抱有希望,他希望李鸿章能采纳他的建议。但石沉海底的上书如一盆冰水及时浇醒了孙中山,他意识到改良的道路在中国行不通,从而走上了积极改造的道路。王开玺教授指出:“主观上讲,人们都不希望天下大乱、血流成河。绝大多数人他们首先选的绝对不是革命,革命是什么,人们生活不下去了,被迫选择革命。但是革命仍然层出不穷,不只是中国,世界各国都有。”
然而,我们不能因为改良之路在中国无处伸展而否认了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立宪派对国体的要求与革命派一致,只是他们把赌注压在了清政府身上。梁启超后来说:“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三)争论,只求真切体悟
以上的争论说到底是源于人们对辛亥革命评价的不同。否定它的人认为:“辛亥革命只是赶走了皇帝,中华民国只是一个空招牌。” 民国成立以来,中国政治局势一直动荡不宁,各派政客争权夺利,军阀混战,地方割据,兼以两次复辟丑闻,始终没有走上宪政正轨,这也就成为近年来一些人非议辛亥革命的理由。这里,王开玺教授提醒我们:“我们要看到客观的历史现象的确是这样的,但搞历史研究的人却要思考,客观历史现象之间的时间先后关系是不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共和立宪对于当时的中国是新生事物,其建设、发展与成熟必须经历相当的过程,所以刚刚告别帝制走向共和的中国,在宪政民主制度建设中出现各种问题、波折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正如王开玺教授所言:“辛亥革命的任务是改变中国两千多年的制度和意识,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
我们不否认“辛亥革命后的社会问题的出现可能与革命党人的处理不当有关系”,但民初“乱象”并不能一概归咎于一场革命。民初的军阀现象,可溯源于晚清中央权威的衰落与地方势力的崛起,辛亥革命更多的是将专制帝国原有的痼疾一下子引发并使之彻底暴露出来。王开玺教授认为:“那些批评革命的人,应该理性地思考一下,我们要做的是把他们未完成的去做好,而不是简单地否定,我们应该去理解他们。”的确,对于那些为国家民族、为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献身的革命者,我们没有立场去指责,没有他们的一小步,哪来后面的大跨步?
提到对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很多人会把海峡两岸学者的研究拿来作对比。王开玺教授指出:“其实大陆和台湾(在有关辛亥革命问题的研究上)有很多相同点,不同之处都是学者个人的原因,这个不同不是以大陆学者和台湾学者两个阵营的形式出现。”他举了台湾学者李敖的例子。李敖曾经评价孙中山,认为孙中山是为救国而卖国。王开玺教授说过:“无论孙中山有什么样的错误,他的领袖地位,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过去中国史学界不约而同地“为圣者讳”,“为贤者讳”,对孙中山正面的东西宣传得多,对他错误的、负面的东西尽可能避而不谈。王开玺教授不赞同这种做法,在他看来,“只要是学术问题就是可以争鸣的。通过这种争鸣,我们才能更客观地去看待它,使我们对其认识更接近客观事实”。因此,应该把李敖的评论看作学术范围内的争鸣。
(四)回首,只为坚定前行
百年辛亥,光辉犹存。100年前,一批革命党人推翻帝制,掀开革命序幕;100年后,一群电影人向时间长河的彼岸眺望,凭借影像的方式还原一个重要时刻的前前后后。在纪念100周年之际,社会上出现一股以影视作品、论文诗集等为主要形式的“辛亥热”。当谈及如何看待这样一种社会现象的时候,王老师这样说道:“从辛亥革命本身来讲,它的意义确确实实非常重大。我们中国的历史很悠久,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而辛亥革命结束了这一制度,这就值得我们加以称道。这是我们国家政治制度的变革,君主专制制度的废除使得西方的一些民主、自由、共和的思想都传入到中国来,对于我们国家的长期发展有深远影响。”现在的社会,我们不再受到君主专制制度及其思想的制约,而现在我们的国人也在享受着辛亥革命的一些成果。而且,“辛亥革命将民主、自由、法制从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世俗精英扩大到了广大群众的层面。”在辛亥革命之前,政治精英、文化精英、世俗精英们也在讲君主立宪,但对广大群众影响不大。在辛亥革命之后,群众也开始谈论民主、自由、宪法、法制、共和,这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天地。
由此我们可以坚信,辛亥革命在我国的历史上有一种不可代替的历史影响,无论是在国家制度方面还是个性解放方面,辛亥革命都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事情,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因此,王老师认为“辛亥热”这个现象是可以理解,也是正常的。但是,王老师还强调,不排除某些不恰当的表现方式混杂在这样原本积极的热潮里,例如某些影视作品为了迎合某些群体的审美品味,刻意虚构故事情节、扭曲历史事实,对此我们应理性地批判。
孙中山先生曾这般展望未来:“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抚今追昔,令孙中山先生忧虑重重的旧中国已一去不返,而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的壮丽画卷正徐徐展开。在这样的广阔背景下,我们重新回首风雨如晦的年代,更加感动于革命先行者关于民主共和的珍贵理想与赤诚热血。(本文转自北京师范大学《春秋人文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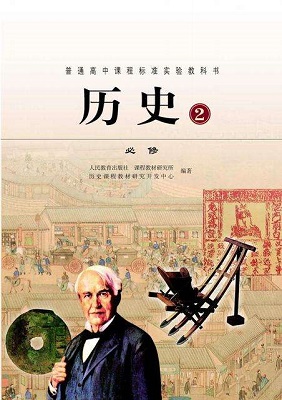






学习下,楼主辛苦了
追忆是一种进步,学习着,前进着
我还以为博主写的呢!没想到是转载!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心怀天下啊
看得我心情澎湃呀~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
历史已经过去,留下来的只有通向未来的路。
那些历史哦革命伟人们已经用鲜血做为代价了,,才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辛亥革命100年??这是一个尴尬的事情。
看到结尾发现了熟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