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念与悲剧----晚清留美幼童命运剖析》是华东师范大学石霓在著名史学家夏东元先生指导下的博士论文增修而成。众所周之,在中国近代化特别是教育近代化的研究著作中关于留美幼童常有提及,如舒新城著《近代中国留学史》、黄利群著《中国近代留美教育史略》等。但是较为系统的研究留美幼童问题的专著却很少,之前的研究多参考容闳的《西学东渐记》,以及美国学者勒法吉(Thomas La Fargue)于1942年出版的《China's First Hundred》。近几十年来,随着一批新史料的发掘,特别是高宗鲁先生搜集整理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使得留美幼童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扩展。而《观念与悲剧》,则是在运用目前所能掌握的史料基础上对于晚清留美幼童较为系统而深刻的研究的一部专著,对于中国近代教育及留学发展的历史研究具有很大的意义。
作者在序言中写到,本书研究留美幼童,是“将留美幼童视作晚清中国现代化的启动的一项重要步骤,留美幼童的诞生及其坎坷不平的人生经历无不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息息相关。本文力图说明一个问题,即造成留美幼童命运的悲剧性的根源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失败的根源是同一的,就是垂数千年不变的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文化世界观。”作者在研究方法上,以留美幼童为明线,晚清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为暗线,贯穿这两条线的则是中国传统的文化中心观。因此,作者把留美幼童放在整个晚清现代化的背景中去探讨,这个视角的把握非常到位,官派留学生赴美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留学计划,而是清政府在近代社会面临的复杂局势下做出的带有被动性的选择,留美幼童的命运时刻和清政府在中国近代化上的态度和措施紧密关联。
本书共六章,第一章论述了晚清时期仍然存在着的封闭保守的文化中心观。开篇并没有直接谈及留美幼童,而是从一种长期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文化观入手,这是本书一个很新颖的地方。这一章内容的价值不在于作者对于这种文化中心观做了多么深刻的阐述,而是在于作者一种宏观的看待问题的视野,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之前尚无派遣学生留学西方的意识的根源,在于“古老中国思想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文明中的巨大惯性”(P.38)。其实,这种惯性在派遣留美幼童以及他们返回国内后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依然在发挥它的影响。

第二章研究了“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的经历以及与留美幼童的关系。作者对于容闳作为边缘人人格的分析非常深刻,容闳一方面具备彻底归化美国的资格,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意识又异常强烈,时刻准备着回国服务。这既是容闳内心的矛盾,也是时代的矛盾,他既是中国近代化的践行者,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者。这个观念的冲突不仅仅体现在容闳的身上,而且体现在之后所有留美幼童的身上。
第三章“异域留学与人格变化”,指出留美幼童赴美前的初年文化养成仍是以传统文化为归依的,赴美后在两种文化的冲突和对立过程中逐渐适应和融合。他们不断丢弃传统中国文化的糟粕,更新代之的是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及现代化的观念,形成了一种“中西合璧式的人格”。第四章“早产与夭折”以及第五章“接纳与排斥”呈现了中国首次官派留学生赴美的全过程,包括派遣赴美留学生计划的提出、实施以及中途夭折直至回国后的待遇。作者运用了大量而全面的史料,对留美过程中的一些细节问题都做了很严谨的分析和考证。第六章“困境中奉献”,作者着重从海军、矿冶、电报、铁路、外交五个方面阐述了留美幼童在各个领域和行业中做出的突出贡献以及对中国近代化的积极的影响。留美幼童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并不等于他们在当时各个行业中所作出的实质性的贡献,而在于他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传播。他们奠定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基础,对于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是深远而巨大的。
利用人格心理学等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来研究容闳和留美幼童的心态,是本书的一大特点,作者尤其对于幼童在赴美留学前后的人格形成及发展做了深刻的剖析。留美幼童在中西文化相融合这个特殊的人生背景之下,其人格深深刻上了时代双重性的烙印。从心理的角度来分析留美幼童,不仅仅是历史学学科交叉的研究趋向在本书中的反映,也是作者试图全面考察留美幼童的一种有意义的尝试。
但是本书还是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关于留美幼童的撤回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石霓在书中指出的原因是“在对待留学生教育的问题上,相当一部分洋务分子的态度和观点与清廷及保守势力是一致的。可以说,他们联合起来,合力扼杀了留美事业”(P.165),作者写到:“在容闳的周围,几乎都是清一色的儒学社会中的循规蹈矩者。”(P.127)并认为陈兰彬、吴嘉善是“怀着对西方文化的鄙视和自卫等复杂心理”。(P132)但实际上,陈兰彬与洋务大员丁日昌交好,曾议及“操练轮船”、“肄业西洋”等事,陈兰彬“辄复雄心激发,乐与所成”。曾、李称赞其“盖有远略而具内心者”;至于吴嘉善,《南丰县志》记载:“同乡枢臣某以嘉善熟悉洋务列荐,……尤好习外洋文字,潜心玩索,虽不通其语言,然竟能翻译。其于化学、算术、机械皆得之文字中,……中国之研究科学者,咸以嘉善为鼻祖。”因此陈、吴二人由于熟悉洋务才会被派遣赴美。只是由于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以及对于西方文化肤浅的认识才导致了与容闳的冲突。
作者在第二章已经研究了容闳的个人经历和在官派留学生赴美计划中的积极促进作用,但是作者仅仅是把目光停留在计划最终得以实施、幼童顺利赴美上。实际上,容闳在幼童留学期间的工作并没有如前期发挥过那么积极的作用。容闳提出留学计划的目的是“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他认为幼童之前已略识诗书,在美国应该以“西学”为主,其用意在于培养一批不同于旧式封建文人的新型知识分子。但是清政府认为必须中西并用,并且把“中学”摆在相对更重要的位置上。本书第四章作者认为容闳不仅没有“纵恿学生荒废中学”,而且“希望学生学好中学”(P.139)。实际上,结合容闳的个人经历和对待中西方的态度来分析,在美国的八年容闳系统地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教育的熏陶,因此对于留美幼童剪辫子、穿西服甚至入教这些行为都不以为然,这些以他的个人经历作对比实在微不足道。但是他恰恰忽略了自己当年出国时的年龄远远大于幼童出国时的平均年龄(据石霓统计在120名幼童中,以11岁至14岁居多,平均年龄为12岁),其基本的价值观已经形成,而且在美国直接进入大学学习,并不像留美幼童汉文基础浅薄,并没有形成中国传统文化上的价值观取向,并且留美幼童生活在美国家庭中,从小学到中学,都无时无刻不被美国文化所直接感染。幼童无心学习“中学”,即使有心学习,在美国环境压力下也实难抗拒。如果容闳督促学生做到了学好“中学”,那么幼童回国后,就不会出现幼童黄开甲在信中描写的刚回家后面临的情况:“我用尽一切语句,甚至指手画脚的哑语向他求情,他仍无动于衷。”由此可见,幼童们在美国并不常用汉语交流,容闳当年留美时也曾写到:“现在无人对我说中文,我很快在忘记中文,尤其是写古文方面。”因此,容闳没有警觉的认识到幼童们在他看来习以为常的变化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认为“况彼等既离去故国而来此,终日饱吸自由空气,……不复安行矩步,此皆必然之势”,并且依然固执己见,影响了清政府既定政策的实施,这也是留美幼童提前被撤回的因素之一。
作者在书中深刻分析了李鸿章、容闳等人物在留美计划上的态度变化,但是缺乏对留美幼童这个主体对象的分析。留美幼童是否都像黄暄桂所写的以“状元榜上标金字,直入皇都作栋梁”作为明确的学习目标,这个很值得研究。他们大部分从小就生活在广东等沿海地区,加之在美国生活的逐渐适应,这种目标不可能具有普遍性。到后期部分留美幼童拒绝回国而在撤回途中伺机逃走,大部分幼童返华后仍然希冀可以重返美国等,都足以说明他们在留美期间世界观、价值观的变化和对待中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
此外,本书在关于留美幼童回国后的工作情况和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上,只选取了有代表性的几个方面,而且论述的时间范围基本上是在留美幼童回国后的十几年之内。留美幼童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的,但同时也是缓慢的。他们在返华后最初的十几年是逐步被世人所接纳和认可的阶段,我们可以适当把视线再往远一点看,20世纪初以后的历史舞台上依然有留美幼童,比如一部分之前隐姓埋名的人一直到民国以后才走入了人们的视野。如果在这方面能够有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同样是非常有价值的。(原创作品,请勿转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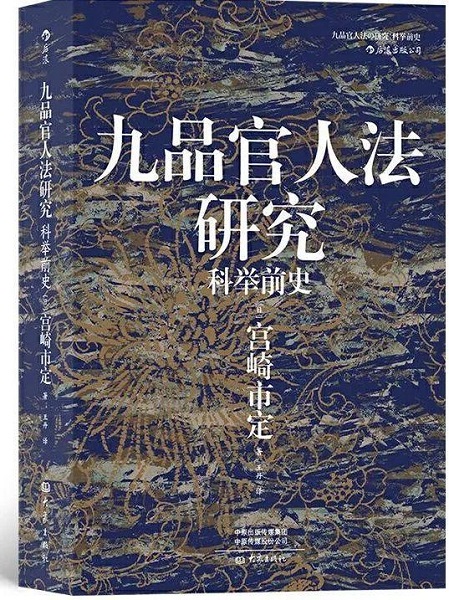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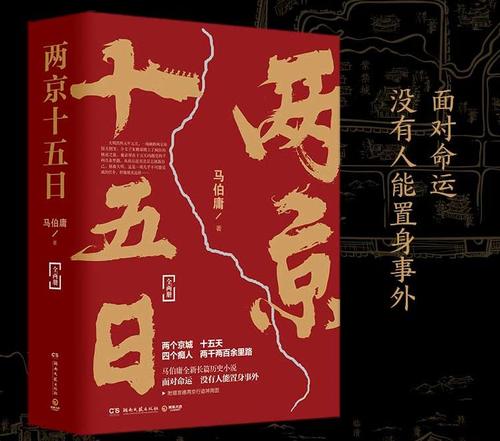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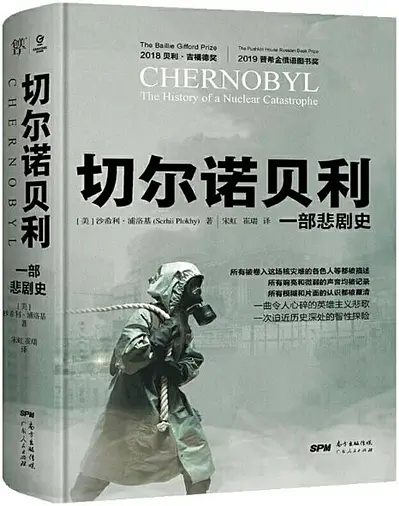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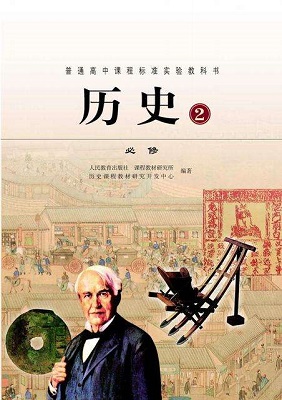

留美幼童带给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的
@蛋糕 恩 CCTV曾经出过5集的纪录片 挺不错的
@iSayme 额 太惭愧了 呵呵
恩不错啊,收藏了!!!
拜读博文,来看看支持一下,嘿嘿
我在电视上有看过关于这些的。
老师好~~向老师学习~~
@马涛个人博客 多谢捧场~~
先留个脚印,慢慢看
拜读过此文。……再拜一次XD
很久没读兴趣外的学术文章啦
写的太好了。
太多字了,我没有看,但我留下一个脚印
@邓肯 唉 我这是为了更新 把平时写的作业都拉出来了 :sbq:
老师就是老师 以后你要是写学术论文的话 估计提职称那是相当的快
叙述的太远了把!
好大一群人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