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关于校庆活动的报道铺天盖地。看着今天清华大学如此风光,我们这些非清华的学生不免开始有点无痛呻吟。于是今天我们学校的论坛上热门话题都和大学有关。记得在观看北大合唱团20周年音乐会后我曾感叹过,北师大百年的文化积淀和老先生们留下的精神财富都随着一栋栋楼旧楼的倒塌而灰飞烟灭了。现在看来这话确实说的有点过分了,也许等我离开师大后才能品味出百年师大的真正味道。每个学生都有关于母校的一份情怀,只不过在离开之后才会感觉更浓。今天在学校论坛里看到一篇很不起眼的转帖,却让我感触颇深。这篇文章的作者曾在兰州大学读本科,现在在北京某大学读研究生。
最近常常想西北,想西北那边夹杂尘土和沙子的灌堂风;想兰州,想兰州遍布深街小巷热腾腾的砂锅和牛肉面;想兰大,想兰大满院子的树和放养在院子里的松鼠; 还有榆中,那个兰州市几十公里外的小县城,就那么被重重叠叠的黄土梁子一道道地围了个密不透风;想搭乘校车必须经过的那三条超长隧道——真是超长啊,不仅 仅是一眼望不到头,而是从你进入隧道开始闭眼,一直等啊等啊,等得都心烦了再睁开眼,还会发现——咦,周围怎么还光线昏暗的一片?
我想这些,控制不住地想,虽然这一切在我在我离开西北,来到现在的这座城市里的这所学校之前,我从未觉得它们会在我的记忆中留下什么烙印,我以为一切都会云淡风轻地过去。
然而突然有一天,那是个晚上,是我来的现在的学校的一个晚上,夜已经深了,我走在现在的校园里,仰望星空——星空很蓝,星光点点。而就是这样一个动作,却足以复活我所有的记忆——这个动作我实在太熟悉了,就是在西北,在一个叫兰大的地方,在一个叫兰州大学榆中校区的操场上,我几乎每天 都会重复这样一个动作——仰望星空,那星空也很蓝,不,应该说更蓝一些,甚至蓝得有些吓人,仿佛要吞掉什么东西似的,而且星光灿烂——让人不经意间就看花了一双眼。不过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因为数星星而看花眼了——虽然月朗星稀也有月朗星稀的美丽。
我不知道其他人如何评价自己的母校,就好像我在这边的一个师姐在提到她的学校是会用到“四大染缸之首”这个词,而之于兰大,我能想到的,却是悲情甚至带有一丝绝望。很沉重,一如西北这边连绵不绝的厚重的第四纪黄土层,又好像金城这座古老城池的历史。
如果要对西北这片土地做一个比喻的话,那么之于我,她像是一具尸体,一具横卧在中国版图一隅的一具白骨嶙嶙的尸体——她荒凉,贫瘠,寸草不生。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片土地上,虽然稀疏却聚集了人烟,千百年来,绵亘不断。而兰大,也一如她身后所依托的这座西北腹地的城市,不可避免地沾染了西北的落寞与苍凉。
我时常会想,还有哪一所学校会像兰大,会像兰大一样这么地招人嫌隙吗?答案是没有的。
我也常常想,还有从哪一所学校里走出的学生,会像兰大的学生这样,对自己的母校抱有这样难以言明的纠结情感吗?我想也是没有的。
因为没有,所以兰大是这样的特殊,兰大人又是这样的难以被理解。
我清楚地记得四年前第一次踏上西北这片土的的情景,那是令人震撼到错愕的一种感情。我不知道在其他学校新生报到是怎样一种场面,在兰大,我看到了有人哭,看到了有人拎着行李径直去买返程车票,也看到花名册上的一些姓名就那么一直空着。有些从南方过来报到的学生甚至不认识西北这边的山,他们竟指着环绕校区周边那些寸草不生的土丘问——那是什么?当回答那些是山的时候,我清楚地看到了他们脸上的表情从错愕转为绝望——也许在他们的概念中山是不可以没有树的,山上也不可以没有石头,山或许还应该是傍着水的,而这边的山看上去更像是一座又一座的坟茔。
所 以每年的迎新之于兰大绝对不是一件喜庆热闹的事情,我也清楚地记得在来到这里的第二年,当我以一个学姐的身份去迎接我的下一级新生时,那是一种多么尴尬的 情景——之于我们,迎新的首要任务不是安顿新生和他们的家长,而是安抚大家的情绪,我记得在我所接下的每一校车的新生面前,我无一例外都会说的一句话就是 ——能在最贫瘠的土地上开出的花朵也许不是最美丽的花朵,但绝是最不平凡的花朵。
其实说到这句话时,我自己都抑制不住地想哭,而大家虽然会喝彩,但更多的除了沉默还是沉默。
不过大部分的人还是选择留下来,选择在这样一片土地上接受四年风吹日晒的雕刻,选择接受兰大那份独有的情结对自己进行晕染。然后,再走出去,再走出去。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早早地就把离开作为自己的目标,比如我,你,他。事实上我们正是为了离开才选择留下,正是因为有着那么一个四年之后可以离开的信念支撑着我们,我们才会安下心在这里没日没夜地拼自己的路,无时无刻不在希冀着这条路是可以顺利通向黄土高原的另一侧的。所以,虽然有些偏激,但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因为这样才有了兰大以踏实著称的学风和以勤奋著称的学生。于是就有了每天图书馆侧门前清晨五六点就排起的长队,和网上流传的疯狂的占座视频。它们都是真实,至少最原始的那个版本是绝对真实的,没有经过半点夸张和修改——因为那些破门而入的动作,那些飞身下楼的动作,那些50米冲刺的动作,甚至是摔倒后又爬起来,都是我们亲身经历过的。
所以就发生了这样一个悖论——我们恰恰是抱着离开的想法延续着兰大“百年不断”的历史,塑造着兰大“自强不息”的精神。于是在中国的高校界有了神奇的“兰大现象”,兰大就这样变成了中国众多高校里一个奇异的标杆,独一无二。但是兰大人都知道的,在所谓的兰大现象背后还有着一个不那么广为人知的更加神奇的词语叫“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兰大心头上的一把刀,也是兰大人不愿言明但却心知肚明痛楚。
其实我想我是没有资格去做任何评论的,虽然我够不上孔雀,但是我知道,我是被影射的,其实,基本上每一个面临毕业的兰大学生都是被或多或少的影射的。因为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选择了离开,理所当然甚至是毅然决然,不留半分商量余地的。特别是在清楚地目睹着兰大的艰难,不,应该说是兰大的窘迫——这些,我们都历历在目。
再没有哪一所高校会像兰大,会像兰大这样——请原谅我在这里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额,会像兰大这样,空有着985和211的名声,空有着一个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空有着院士,长江学者却依然为了留住本校的生源而挖空心思,费尽心机。因为没有人情愿来这边,人们印象中的西北永远是和荒芜闭塞挂了钩的——而事实也确实是这样,而来了的,也都纷纷离开了,留下的只有整个校园的落寞。
我时常想如果兰大真的是一位母亲的话,那么我们这些“子女”到底算什么?
我清楚地记得就在刚刚过去的那个春夏之交,在我忙着张罗自己的前程的时候,我无比纠结的心情。偏巧这个春夏之交又是这样的多雨,于是我不止一次在校园里走着走着然后开始发呆。甚至有那么一次,在我找学院领导谈话的一次,我差一点就要说出——我不走了的话了——虽然我知道我终究还是会走的,所以不管是差一点,还是差一点点,我终究说不出口。
因为我太明白了,终究,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员,图的也只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谋一个生计而已。和真正代表了兰大脊梁的那些前辈们相比,我,我们大概永远只能是自惭形秽的兰大过客。我们也许是善良的,甚至不能算是没有良心,因为离开的的大部分人大概都想着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再回来,为兰大做些什么,但是我们永远都高尚不起来——我们只 是普通人,也只能做普通人的选择——高尚的代价太惨重,事实上高尚的背面其实遮盖着赤裸裸的残酷,这一切,作为个体的我,你,他,以及我们的家人和其他所 有站在我们身后的人,都承担不起。
这也许就是现实,随着年龄与日俱增的现实,就好像在大学期间的支教,所有的人无一例外都是抱着最崇高的想法和最热烈的心情来到那些几度被遗忘的角落,然而现实终究是现实,有时候现实的强大足以击碎所有的热情和理想——我不知道其他学校的支教 是怎样一种情形,但是在兰大,在西北这边,支教有的时候意味着不明原因的低烧,脱头发,甚至更加严重后果。
所以我们中的大部分都选择离开,也许是退缩吧,懦弱地退缩。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只能就这样,没有解释,渐行渐远。
所以兰大注定是悲情的,我想,这是宿命,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兰大也是包容的,她赐予了从她身边走过的每个人以沉重的礼物,里面有宽容,有坚忍,以及磨灭不掉的烙痕,她让我们知道生命其实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可以残缺并美丽着,可以贫瘠却无比丰富,然后看他们上路。
(谨以此文悼念那些逝去的青葱岁月——它们被永远隽刻在西北一个叫兰大的地方)
兰州大学在几年前就将本科生全部搬到了榆中县——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虽然我没有在兰大读书,但是在这里生活的苦我有深刻体会。从小就被家长教育要好好学习,离开这个偏僻荒凉的地方。7年前高一班主任要求每人写下自己的奋斗目标,我写的是“离开这里,考到北京”;4年前我成功地从那里走出来,到北京求学;可是命运就是这么捉弄人,现在我又要回到那里去了。在毕业季里,令我觉得伤感和悲壮的,不只是要离开北师大了,而且是又要回到家乡去了。我的人生目标又一次变成了7年前的那句话,虽然这也许要等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我不过是芸芸众生中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一员,图的也只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谋一个生计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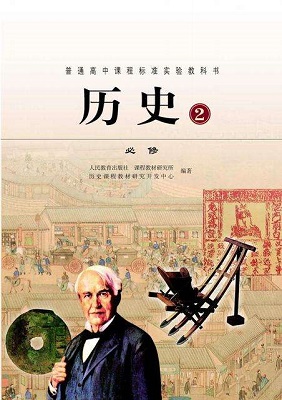

@Japhia
说是这么说,学风扎实,不过好像不小心就耐不住寂寞学偏了,然后学出来发现认识神马的和实际还有很大差距,杯具的兰大啊。。
@guishan 对啊 感觉就是荒山野岭的~~不过远离闹市区 非常清静 适合学习啊
@Japhia
传说中出校门便是一片包谷地哈,看来你果然是也该感慨下哈哈。。
@guishan 就是榆中那边~~ :sbq:
@Japhia
不会是榆中那个吧,哈哈,不过我没去过,本部倒还熟。。
@guishan 是的呢~家就在兰大附近
莫非是甘肃人哈 。。
@Japhia

侧栏tab切换 就是我的那个最新评论 最新文章.随即文章.三个共用一个框.鼠标放在哪个上面就显示哪个.你去看看效果咯.
灰常节省空间哦.
@ISayMe 侧栏TAB切换是神马东东?我还不太懂啊~
@钱侃部落格 我的大学生涯也接近尾声了。。。同时毕业季的人啊 伤不起
名校就是好啊
大学好玩啊 就是时间太短了 我的大学生涯已经接近最后的尾声了
清华校庆大事哦!
俺还没有什么想法呢.嘿嘿.
服务器抽风了.最近很有压力啊 :jiong: 准备好的东西都没法往上贴啦.服务器恢复后把侧栏的tab切换写上
昨天看了电视!呵呵!
看主席讲话了,讲的很不错。
最近清华校庆的文章很多啊~~